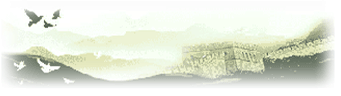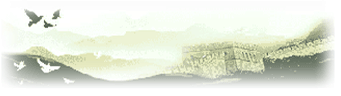漫谈典故与用典(蔡秋华)
古往今来,但凡名家高手,写诗填词著文皆好用典故。何为典故?典故就是“指典例故实而已,今则凡见诸古籍,而为后人袭用的,统称为典故。”﹙参见《常用典故词典·序言》﹚据此而言,典故有狭义和广义之分。狭义地说,单指“典例故实”,广义地说,除了典例故实,还包括古人的名言佳句。相比而言,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等工具书为此所下的定义“诗文等所引用的古书中的故事和词句”相应要简洁得多。
不言而喻,若以典源固有的属性看,典故似可分为事典和语典两大类。而依“陈古讽今,因被证此﹙元朝杨载语﹚”的功用看,两者本无优劣、轻重之别,前人的用典实践早已证明了这一点。试以中华书局编审李肇翔先生选注的《辛弃疾词》为例,该书正如编者所说,“精选那些得到读者广泛传颂的作品,同时兼顾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,力求将辛词最精粹的部分奉献给读者”,说明辛词选注本所选篇目无疑具有代表性。现存辛词六百余首,上述选注本收编稼轩词一百七十八首,是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集辛词之大成者。故笔者有兴趣做了一番较为翔实的统计,结果是该选注本累计用事典近三百例,语典二百五十多条,两者几乎是平分秋色。
有必要强调一下的是,有些语典自身并不纯粹,也就是说,此类语典中还蕴含着与之相关的事例或史实。如辛词鹧鸪天﹙木落山高一夜霜﹚中“为谁春草梦池塘”句,典出“池塘生春草”,本属语典。然而其又内含着谢灵运因梦见其族弟谢惠连而偶得“池塘生春草”句一事,辛弃疾正好借此用来曲折表达自己思念族弟之情。又如,添字浣溪沙﹙记得瓢泉快活时﹚“断送老头皮”句亦为语典,却缘于史实:宋真宗东封泰山后,广招天下隐士入朝为官,一次,真宗问杨朴临行时是否有人写诗为其送行,杨朴说他妻子曾写诗为之送行,中有二句云:“今日捉将官里去,这回断送老头皮。”真宗听罢哈哈大笑,挥手让杨朴重返田园。这首词作于他福建安抚使任上,辛弃疾自知前途未卜,引用此典,寓庄于谐,将自己“外以诙谐自嘲之趣,内含郁闷悲苦之情”的矛盾心理永远留在了史籍上。
再者,语典还有袭用和化用之分。所谓“袭用”,就是将前人说过的话语一字不落地抄录沿用于自己的诗文中。如卜算子﹙千古李将军﹚中“舍我其谁也”句,语出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“如欲平治天下,当今之世,舍我其谁也。”词人沿用此句,直抒自己因南宋小朝廷苟且偷安、抗金复国之志不能实现而既无奈又不甘的悲愤心情。词人袭用现成的古人名句,却毫无做作之感,充分反映了辛弃疾炉火纯青的词学造诣。“舍我其谁也”算得上是尽人皆知的一例,故不再另举成例。有趣的是,古人写诗填词有时会整首袭用前人的名言佳句,由此而成的诗篇词章称为集句体。一般来说,凡袭用儒家经典的称作集经句,袭用范围大于此的称叫集古句。王安石晚年做了许多首集句诗,最长的达百韵。文天祥生前最钦佩杜甫,竟撰有二百首集杜诗。集句体词也并不少见,最著名的要数辛弃疾的忆王孙:登山临水送将归。悲莫悲兮生别离。不用登临怨落晖。 昔人非。惟有年年秋雁飞。五句分别袭用自宋玉的《九辩》、屈原的《九歌》、杜牧的《九日齐山登高》、苏轼的《陌上花》和李峤的《汾阴行》。五句连续袭用,一气呵成,可谓“一经运用,便得风流”。
所谓化用,就是不拘泥于原句,着意化而用之。﹙清﹚黄景仁《少年行》诗云:男儿作健向沙场,自爱登台不望乡。太白高高天五尺,宝刀明月共辉光。这首诗塑造了一个胸怀大志朝气蓬勃的从军少年的形象,言说男子汉应当鼓起勇气振作奋发奔向沙场,立志从军入伍登台拜将不留恋家乡,意气高扬如高高的太白山直插云霄,让宝刀在明月夜发出杀敌的寒光。诗中“太白”为山名,在陕西省眉县东南。“太白高高天五尺”化用《三秦记》中“武功太白,去天三百”“城南韦杜,去天五尺”两句,别出心裁以山高喻少年心气高昂,不能不说是着意而化用之的典范。
化用也是词家填词时常用的技法。笔者以为,最值得推崇的当是辛弃疾的《酒泉子·无题》一词:
流水无情,潮到空城头尽白。离歌一曲怨残阳,断人肠。 东风官柳舞雕墙。三十六宫花溅泪,春声何处说兴亡,燕双双。
难得的是整首几为化用而成。“流水”二句化用唐刘禹锡《金陵五题·石头城》中“山围故国周遭在,潮打空城寂寞回”两句;“离歌”二句化用唐岑参《酒泉太守席上醉后歌》中“胡笳一曲断人肠,座上相看泪如雨”两句;“三十六宫”三句分别化用骆宾王《帝京篇》中“汉家离宫三十六”、杜甫《春望》中“感时花溅泪”和周邦彦《西河·金陵》中“燕子不知何世……相对诉说兴亡”句。之所以说值得推崇,是因为它突破了一般送别词单为离愁而作的窠臼,更在于怀古伤今,抒发了沉重的兴亡之感。而且可以这样说,如果不借助化用技法,实难以成就本词沉郁雄浑的词风。
古人写诗填词用典,看似信手拈来,实则他们无不都遵从“用事以不露痕迹为高﹙参见清王士祯《带经堂诗话》﹚”和“僻事实用,熟事虚用﹙语见姜夔《白石诗说》﹚”两大原则。仅以本文所提及的典例,已足以说明古人用典多有“不露痕迹为高”的自觉性,对此就不另赘述。
至于“僻事实用,熟事虚用”,辛弃疾堪称斵轮高手,仅以其绝笔词洞仙歌﹙贤愚相去﹚就可资一二:贤愚相去,算其间能几?差以毫厘谬千里。细思量:义利舜跖之分,孳孳者,等是鸡鸣而起。 味甘终易坏,岁晚还知,君子之交淡如水。一饷聚飞蚊,其响如雷,深自觉,昨非今是。羡安乐窝中泰和汤,更剧饮无过,半醺而已。词中“安乐窝中泰和汤”用典生僻。经查,典见《宋史·邵雍传》,谓邵雍“名其居曰安乐窝,因自号安乐先生。旦则焚香燕坐,晡时酌酒三四瓯,微醺即止,常不及醉也。”此时的辛弃疾早已看透世情,“半醺而已”实实在在是他生命行将结束之前的真实写照。反观“君子之交淡如水”,此典妇孺皆知,辛弃疾晚年也确实常以此自勉,然而,后人可以想见,在他垂暮之年回首一生时,残存其内心的那忠而被谤的隐隐之痛又岂能全部忘却?这不能不说是“熟事虚用”的范例。
综上所说,古人写诗填词著文用典,或为了品评历史以托古喻今,或为了抒情言志以表明心迹,或为了丰富内涵以言简意赅。而用典贴切精当,确实可以为自己的文学作品增添不少笔墨之趣,诸如典雅之情趣,含蓄之幽趣,言简之妙趣,思远之志趣。因此,古人写诗填词每每为用典费尽心机而乐此不疲,成为千百年来炎黄文学界所特有的一川风月。
记得英国人瑞恰兹在其《文学批评原理》一书中这样说过,“有时候,读者方面不知道出典无关紧要,不会妨碍他们把握作品的任何主要部分。而如果能知道出典,则会对作品作出更充分的反应和更深刻的领会。”窃以为,碧眼黄髯儿此话所言极是。
(摘自《诗词之友》2015年第4期总第75期) |